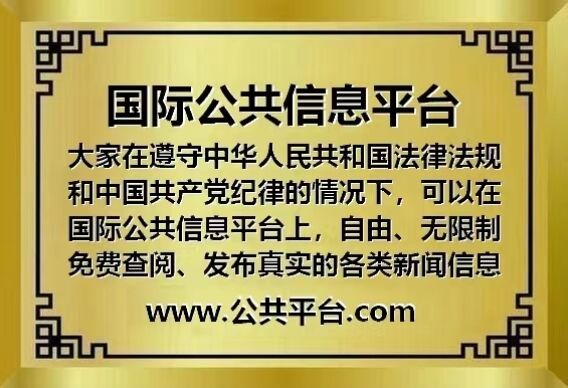|
|
陈中华:把病人晾手术台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故意杀人重大刑事问题
近日,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肖飞因婚内出轨多人被妻子举报,引发社会关注。随着调查深入,事件核心已从私人道德争议,逐步演变为对医疗行业职业伦理、人才培养机制乃至公共安全的深度拷问。 一、手术室里的“特权庇护”:生命安危竟成私人情分的注脚 在举报信披露的细节中,最令人震惊的并非婚外情本身,而是肖飞为维护情人董袭莹,在手术过程中与护士争吵、强行更换医护人员,并擅自离开手术室长达40分钟,置麻醉状态的患者于无人监护的险境。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临床麻醉管理规范》中“麻醉医师不得擅自离开手术间”的明文规定,更暴露出部分从业者将职业权力异化为“私人庇护工具”的危险倾向——当手术台成为权力博弈的秀场,当患者生命成为情感纠葛的牺牲品,医疗行业的专业信仰与公众信任正被公然践踏。 值得注意的是,涉事女主角董袭莹的职业路径同样疑点重重:1997年出生的她本科就读于美国巴纳德女子学院经济学专业,回国后“跨界”学医,通过北京协和医学院“4+4”学制(即4年非医学本科+4年医学教育)仅用四年便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随后直接进入三甲医院。这一轨迹与公众认知中“医学培养周期长、门槛高”的常识形成强烈反差,也难怪舆论质疑其学历背后是否存在“特殊通道”。 二、“4+4”学制争议:精英培养还是特权通行证? 协和医学院“4+4”项目本是探索医学教育改革的创新举措,旨在培养“医学+X”复合型人才。但董袭莹事件中,公众的质疑集中于三点: • 专业能力速成化:从经济学本科到医学博士仅用四年,如何确保其临床技能、解剖学等基础课程的扎实掌握?医学人命关天,容不得“跨界速成”。 • 选拔公平性存疑:该项目招生是否存在“隐形门槛”?非医学背景学生与传统医学生竞争时,是否存在推荐信、导师资源等“软指标”倾斜? • 职业路径特殊化:普通医学生需经历5年本科、3年规培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进入三甲医院,董袭莹的“四年直升”是否存在制度外的“加速通道”? 这些质疑的本质,是公众对优质医疗资源分配公平性的担忧。当顶级医院的执业资格成为少数人的“捷径”,普通医学生的十年寒窗便失去了价值尺度,医疗行业的专业性和公信力也将遭受侵蚀。 三、双院协同调查:打破“自查自纠”的公信力困局 事件涉及中日友好医院(用人单位)与协和医学院(培养单位)两个顶级医疗体系,二者既有业务关联又相对独立,若仅依靠内部自查,难免陷入“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窠臼。建议由国家卫健委牵头成立第三方调查组,重点核查两方面问题: 1. 手术违规操作的法律定性:肖飞、董袭莹在手术中擅自离岗的行为,是否涉嫌《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医疗事故罪”或《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的医疗损害责任,以及故意杀人罪,需司法机关介入厘清责任。 手术台上的患者,如同待护的幼苗,每分每秒都依赖医护团队的专业守护。当麻醉生效,患者失去自主意识,医护人员便成为其生命安全的唯一屏障。然而在这起事件中,医护人员董袭莹、肖飞因操作争议与护士发生冲突后,竟置患者安危于不顾,擅自撤离手术室长达40分钟。 这40分钟里,麻醉中的患者无人监护:麻醉药效可能引发的呼吸抑制、出血风险、体温异常等致命隐患无人处理;手术切口暴露可能导致的感染风险无人防控。他们的行为,本质上是将患者置于“无防护死亡区”,与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行为具有同等的主观恶性和现实危险性。有人认为,该事件属于医疗事故或职业伦理问题,但这种认知严重低估了行为的危害性。 • 主观故意清晰:医护人员明知离开手术室将导致患者失去必要监护,仍为泄私愤故意为之,符合“明知可能造成危害后果而放任发生”的间接故意特征。 • 客观危险紧迫:手术室是高度专业的医疗场所,脱离监护的麻醉患者随时可能因突发状况死亡,行为已制造了现实、紧迫的生命危险。 • 法律依据明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虽未造成患者死亡结果,但这种将他人生命置于极端危险境地的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未遂或中止)的构成要件。 2. “4+4”培养过程的合规性:调取董袭莹的入学考试成绩、课程考核记录、临床实习档案等原始材料,核查其是否符合“完成规定学分、通过执业医师考试”等硬性标准,排除“学历镀金”嫌疑。 同时,应借此机会完善医疗行业两项制度: • 建立“手术安全哨”机制:通过电子围栏、实时监控等技术手段,确保主刀医师、麻醉师在手术期间全程在岗,违规离岗即触发警报。 • 推行医学教育背景公示制度:对非医学本科出身的执业医师,在医院官网、病历系统等显著位置标注其教育路径,接受患者和同行监督。 四、医疗行业的“刮骨疗毒”:比医德更重要的是制度防火墙 此次事件撕开了两个残酷现实:其一,部分医护人员的职业伦理已脆弱到不敌私人情感;其二,看似严密的医疗管理制度,在权力或人情面前仍有漏洞可钻。要重建公众信任,需从三方面破局: • 职业准入“去特权化”:医学教育必须回归“以临床能力为核心”的考核标准,任何背景的学生都需通过同等强度的实操考试、病历书写考核,杜绝“学历光环”掩盖专业短板。 • 医疗安全“零容忍”追责:对术中擅离职守、篡改病历等行为,除行业处分外,应纳入《医师法》的“终身禁业”条款,情节严重者追究刑事责任。 • 公共监督“可视化”升级:推动三甲医院手术间监控录像可追溯、可查询,建立患者家属“术中知情权”制度,关键操作需向家属实时通报。 当手术刀不再是权力的延伸,而是生命的守护者;当医学博士的头衔代表的是千万次解剖实验的积累,而非学历镀金的捷径,医疗行业才能真正回归“救死扶伤”的本质。肖飞、董袭莹事件不应仅是一场舆论风暴,而应成为医疗体系自我革新的契机——唯有以制度刚性筑牢职业底线,才能让每个躺在手术台上的人,都能相信自己托付的是专业,而非特权。 当手术刀成为挽救生命的工具时,它是文明的象征;当医护人员成为生命威胁的制造者时,必须接受法律的严惩。把患者晾在手术台上的40分钟,暴露的不仅是个别从业者的医德沦丧,更是对法律底线的挑战。唯有以刑事追责的雷霆之力,才能让手术室回归“生命圣地”的本质,让每个躺在手术台上的人,都能在法律的庇护下迎来重生的希望。这不仅是对个案正义的追求,更是对整个医疗行业法治根基的重塑——生命面前,没有任何职业可以例外。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