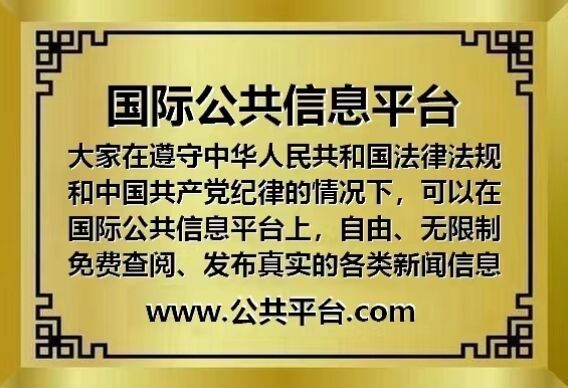|
|
陈中华:法官审判公平正义,才能防止被打被杀
法官法第六条明确规定:“法官审判案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这里所提及的事实,并非一方片面口述的事实,而是由相关证据充分证明、完整呈现出来的事实。当证据无法证实当事人所陈述的事实时,那么该事实便不能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事实。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法院的法官王佳佳惨遭党志军杀害,这又是一起发生在司法工作人员身上的恶性事件。本应是令人悲痛万分的故事,我们理应一致痛斥行凶者的暴行。然而,在评论区却出现了出奇一致的声音,大家都急切地想知道行凶的缘由,进而在针对这一行凶原因的探讨中,思考究竟是该痛斥行凶者,还是对其产生同情。 对于一个杀人犯,为何人民群众会表现出如此出奇一致的“双标”态度呢?作为业内人士,心里清楚,并不幻想调查结果会让一个已逝之人背负枉法裁判的罪名,从而赋予行凶者所谓正义的理由。但凡稍有社会阅历的人都明白,这种情况绝无可能出现。 法官被杀案并非首次发生。回顾近年来的情况,法官遇害案件并非个例。从2016年北京昌平女法官马彩云被害,到2017年广西陆川县退休法官傅明生遇害;再到2020年哈尔滨市双城区法官郝剑、2021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周春梅相继遭遇不幸,每一起案件都令人痛心疾首,深感惋惜。 法官遇害案绝非仅仅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其背后更是一场深刻的人性反思。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人性中的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在追求正义的艰难征程中,我们不仅要勇敢地面对外部的诸多挑战和困难,更要直面自己内心深处的挣扎与抉择。 所以,大家真正应该关心的并非仅仅是这个案件本身,而是案件发生之后所带来的更为深远的影响。比如,法院的安检措施是否会变得更加严格?类似的悲剧事件是否会再次发生?是否能让老百姓拥有更多机会走进法院旁听庭审,让更多的审判通过网络直播接受全社会的广泛监督,从而让每个人都能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只有在审判过程中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才能让枉法者无处遁形。这不仅能够促使监督机构早于行凶者介入类似案件,揭开司法审判那层神秘的面纱,减少公众的误解,还能让更多法律人在案后进行释法工作,有效消解仇恨与对立情绪。更重要的是,能让那些在权力中迷失的审判者清晰地做出选择:是坦然运用权力维护公平正义,还是甘愿自担风险换取非法利益? 以马彩云被杀案为例,有网友评论道:“男方婚前盖的房,女方出轨,要离婚,法官判为共同财产,把男的惹急了,把法官、女的、女的新男人都杀了,然后自杀了”。这或许是一种错误的认知,但当时有没有人耐心地为其解释为什么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呢?倘若有人能为其做好释法工作,及时化解矛盾,或许这场悲剧就能够避免。 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案子,马彩云将原本不属于女方的一套房子判给了女方。若不是中院和重审的法官纠正了这一错误,男方会认为自己输得毫无怨言吗?我们又有谁真正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思考过呢?公正的案件,无需惧怕评论。我们希望社会能够认识到,倘若没有司法作为公正的坚实底线,任何人的生命都将得不到切实保障。 另外,敢于报复法官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发生极端个案难以完全避免。但如果我们将每一个极端案件都进行过度推理,并由此及彼,推论成普遍现象,那么国家的法治思维必然会出现严重问题。法官受到暴力伤害,法律人悲愤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绝不能因为悲愤就将事件的影响无限放大到令人恐惧的程度。一旦允许这种放大,就会因为某一个极端事件,将一个社会群体卷入其中,必然会造成更加恶劣的社会影响。 过去,法院允许当事人自由进入,群众和当事人与法官见面也较为容易。但前些年发生了一起法官被爆炸案之后,各级法院纷纷加大安保力度,购置了价值不菲的安保设备,增加了大量安保人员。这使得老百姓进入法院时,会明显感觉到壁垒森严,而许多法院的安保人员将来访的人民群众视为敌人,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即便律师也深感不便。 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显然并不可取。 如果将每个极端案件都推断为是对社会的挑战,对社会某个执法层面的挑战,恐怕国家的法治将会遭到严重破坏。若把每个不同层面的极端伤害案件都如此扩大化推论下去,就会出现法治概念被偷换的情形,届时恐怕人人都将不得安宁。在此案中,法官的权利理应依法得到保障,其他被杀害和被伤害的公民权利同样应该依法得到保障。 所以,将法官遇害简单推断为是对法院的挑战,这种思维是不应该出现的。法律强调的是法治,法治保护的是全民的利益,法官也是公民的一员,应该得到同样的保护。法院并不等同于法律,法官也不等同于法律,不能将保护法院和保护法官与保护法治完全等同起来。 其实,法官唯有做到审判公平正义,才能有效防止被打被杀。法官被打被杀的事件在中国并非新鲜事,曾有犯罪嫌疑人身捆炸药在法院炸死多名法官。 同样,中国存在部分法官枉法裁判的现象也不是新闻,这种事情发生率较高,几乎为所有国民所痛恨。法律缺乏公信力,法官不受人尊敬,这是法官被打被杀的首要原因。所以,法院进行深刻反思远比严惩打杀法官者更为重要。 2015年9月9日,在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大楼内,该院民三庭法官刘坦、郑飞依法为已经审结的一起劳动纠纷案件的上诉人胡庆刚送达法律文书并进行判后答疑时,被胡庆刚突然持刀刺伤,法官刘占省、胡韧先后上前制止也均被刺伤,其中法官郑飞伤势严重。这起《胡庆刚诉十堰方鼎汽车车身有限公司劳动报酬纠纷案》,原本是一起一审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担任此案一审的法官名叫李润青。下面,让我们看看此案究竟简单到何种程度,为何十堰一、二审法院的法官会判令原告胡庆刚败诉。 在一审判决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原告的诉讼请求是,2013年8月13日,原告经人介绍进入被告方鼎汽车车身公司处上班。工作期间,被告经常拖欠原告的工资,且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未给原告购买社会保险,2014年2月23日,原告不得已离开了被告方的公司。综上,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双倍的工资和加班费及拖欠的工资与社保金,合计66000余元。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提供了五组证据:1.员工请假表;2.考勤证明;3.易新华签字的书面证明材料;4.银行账户明细;5.方鼎汽车车身公司的工作服。 被告的辩称是:原被告之间从未建立过劳动关系,原告未给被告提供过劳动,被告的员工花名册上没有原告的名字。故而,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院支持。 为此,被告出具了三组证据:1.支持被告主张的仲裁裁决书;2.方鼎汽车公司的工作服;3.职工花名册。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名叫李润青的法官是如何下达他的判词:“本院认为:原告胡庆刚提交的考勤证明系复印件,原告胡庆刚也不能说明该证据的真实出处,对于银行卡明细也不能证明记载的款项系被告方鼎汽车车身公司支付的。故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的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对于原告胡庆刚的各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庆刚的各项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胡庆刚负担。” 这起简单到连普通人都能轻易裁判的案件,为何会被十堰的两级法院处理成一起最终导致四名法官被人搏命刺杀的惊天大案呢?其根源就在于十堰的劳动仲裁机关和两级法院,完全违背基本常识,罔顾最基本的正义,不为弱势人群主持公道,沦为了人们口中的“黑衙门”。这起案件若由有良知和常识的人来审理,只需问一句:原告提供的银行卡明细中,是否有被告支付的款项?这些款项为什么被告要支付给原告? 如果被告据实回答,那么此案的事实立马便可得到证实:原告与被告,确实存在过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如果被告撒谎,称这些银行卡明细中没有自己支付的款项,那么可以立马休庭,给原告律师出具法院的协查函,请原告律师去银行核实这些银行卡中的钱,是否存在被告账户中支付的款项,如此案情也能大白于天下。至于在起草判决书时,被告应支付多少钱给原告,可参照当地的劳动市场行情加以确定,并不难设定一个合理合适的数额,这样此案自然可尘埃落定。那么,后来在十堰中院发生的四位法官被杀案,还会发生吗? 然而,令人感到荒诞透顶的是,李润青的一审荒唐判决居然得到了十堰中院的法官们毫无保留的支持。最终导致绝望的胡庆刚以命相搏,选择与这些缺乏常识的法官们同归于尽。这四个被刺伤的法官,真应该庆幸他们碰到的是个业余杀手,倘若换了像杨佳那样专业的杀手上场,估计他们早就命丧黄泉了。 也就在这起四位法官被当事人刺杀的案件发生之后,众多法官、律师和公众,都从法院的安检形同虚设,法官也是弱势群体,司法为何得不到尊重等等角度,分析此案的后果并试图从中得出经验教训。诚然,这些原因固然是导致此案发生的部分因素,但显然并非最主要的原因。 相信任何一个拥有起码常识的人,都不难发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十堰的两级法院,是一群缺乏最基本常识的人在主导审判工作。 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四名法官被刺伤之后,十堰中院的一位处级干部面对央视的镜头,居然还能恬不知耻地说,当事人胡庆刚的司法救济渠道并未穷尽,他还可以走申诉程序提供新证据获得案件的再审云云。 一个帮资本家打工,且从银行卡明细中就能够确证这种雇佣被雇佣关系成立的简单案件,还需要什么新证据来证明这种关系成立呢?胡庆刚有能力喊来自己的工友们,证明他在这家黑心的资本家公司里劳动过吗?那些出庭作证的人会冒着失去饭碗的风险帮他吗? 从这起案件中,我们自然可以看到绝望者的反抗缺乏理性,但胡庆刚至少比去幼儿园屠杀幼童的郑民生脑子要清醒,他知道冤有头债有主的道理,不会找错行凶的对象。尽管他必须为自己用犯罪的方式刺杀法官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很多人为他的暴烈反抗点赞也并非毫无道理。 毕竟,十堰两级法院的司法沉沦,才是导致这起法官被集体刺伤的案件偶然发生在十堰中院的核心原因。中国的各级法院及其法官们若不从这起法官被刺杀的案件中接受血的教训,在今后的审判实践中继续罔顾基本常识,无耻地偏袒有钱有权的人,下次也许自己就会成为被刺杀的目标。如果中国的法官只能听懂暴力这一种语言,自然会有步胡庆刚后尘的人,继续用行动告诉他们这个道理:当法院及其法官不践行公义的时候,自然正义女神必然会上场找到她想找到的对象。 法官应该是充满智慧的,具有敏锐洞察力和良知的人,绝不能做呆若木鸡、昏庸无能的“葫芦官”。从判决书可见,本案一审法官显然不能胜任这个职业,应该下岗。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选择搏命去刺杀法官的当事人胡庆刚,之所以不想活了,要带几个法官去垫棺材,其犯罪的动机,无疑是想凭借常识证明自己跟资本家打工的事实,竟然遭遇黑心的十堰一、二审法官一而再的凌辱,才选择与法官们同归于尽的方式来终结自己活着不如死去的悲惨残生。 从胡庆刚刺杀法官案血写的教训中,所有掌权却胡作非为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当一个被权力凌辱的人不想活了之后,是不会去上访的,他会选择犯罪来终结自己的人生。对那些良知未泯的弱者如胡庆刚之辈而言,他们不会去幼儿园、中小学或公交车上,通过制造恐怖事件来加害其他无辜弱者,而会按照冤有头债有主的自然正义原则,去找到加害他的恶人或恶势力寻仇雪恨。从某种意义上说,胡庆刚有理犯法刺杀法官之举,也是对我们这个走上岔道的社会做出的另类贡献。尽管他确实是个持刀伤人的罪犯,但他无疑是个值得尊敬的罪犯,有理由接受众多被沉沦的司法伤害的弱势人群,发自内心给他点赞。 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重要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是,一些从事司法工作的人,依然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有案不立、压案不办、有法不依。前些年流传在民间的顺口溜:“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所描述的现象至今仍未完全杜绝。 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司法工作人员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遭受牢狱之灾,甚至失去生命!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司法不公,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 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是早已被历史证明的结论,但是如今许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两千多年前的《左传·曹刿论战》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话说当年齐国大军攻鲁,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来应战。庄公先说了两点:一是衣食这类养生的东西,我不敢独自享受,一定把它分给别人。二是祭祀用的猪、牛、羊、玉器和丝织品,我从来不敢虚报夸大,一定按照实情相报。但曹刿认为这只是小恩小惠和小信用,据此并不能取胜。最后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明察,我一定会按照实情处理。”曹刿这才放心:这是尽了本职的一类事情,可以凭借这一点去应战。许多人事后总结说鲁国之所以取胜,是因为鲁庄公采纳了曹刿关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战术理论,这其实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视了司法公正在凝聚民心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反面的例子是清末的多次对外应战。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人民法院无疑就是这道最后防线的终极守护者,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有些地方法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判决造成了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申诉,申诉再申诉,导致信访局门庭若市,造成有些状告无门的人,自行执法,甚至自杀性报复社会滥杀无辜。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决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要严惩不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社会才能稳定发展,党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而长期执政。 法官审判公平正义、才能防止被打被杀。希望通过党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绝对全面领导、通过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开展、通过司法改革的推进,人民会慢慢发现,打官司不用再求人了,法官不再生冷硬了,当一份份判决都得到信服,法治精神成为普遍信仰,败诉方不会再怨恨法官,到那时,法官群体才称得上真正的安全。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那个美好的画面:当法官踏出法院大门的一瞬间,斜刺里闯出一个老汉,手中握着的不再是剔骨钢刀,而是一捧鲜花。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