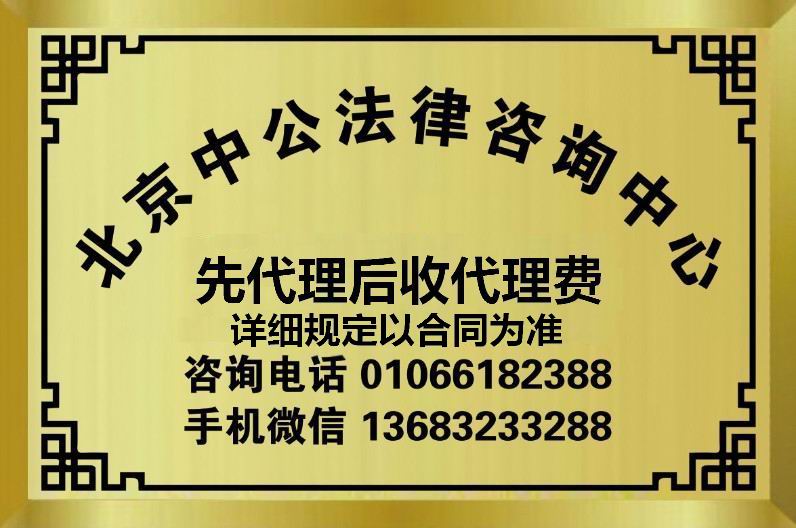|
|
陈中华:吁请最高的人民法院,对张扣扣案启动再审
"为母复仇" 的退役军人张扣扣因故意杀人罪二审被判死刑,此事引发舆论强烈震荡。公众对张扣扣的深切同情与对判决的争议,不禁让人联想到此前的于欢案 —— 山东少年于欢目睹母亲遭讨债者羞辱,警方到场仍未解除拘禁,绝望中刺死一人,一审无期徒刑引发众怒,最终山东高院改判五年有期徒刑。这一转折虽基于事实,却也离不开舆论对公平正义的呼唤。正因如此,张扣扣案初现时,舆论几乎一致将其视作 "又一个于欢",期待司法能兼顾法理与情理。 在我看来,司法机关审理张扣扣案,当置于天理、国法、人情的坐标系中综合考量。任何刑事案件都非孤立存在,司法不仅要审视案件本身的事实,更需剖析其背后的深层成因。给张扣扣一线生机,震慑的是恃强凌弱者,守护的是社会公平正义,更能为法治建设注入良性推力。一个案件的审判,看似与个体无关,实则为每个公民树立着法律与正义的标尺。最高人民法院应启动再审,理由如下: 1. 张扣扣是在杀母凶手未得到法律应有制裁、其父多次上访无果的情况下,才对凶手实施报复的。1996 年其母被害后,凶手仅服刑四年多便出狱,且从未道歉,张家多年维权未果,这成为埋藏二十余年的仇恨根源。当法律渠道彻底失灵,个体对正义的渴求便可能走向极端 —— 这不是对暴力的纵容,而是对司法救济缺失的反思。 2. 张扣扣没有滥杀无辜,且主动投案自首。其复仇对象明确指向当年涉案人员,作案后未逃避责任,显露出对底线的坚守。这种 "不牵连无辜" 的克制与 "愿承担后果" 的担当,与滥杀泄愤有着本质区别,理应在量刑中得到体现。 3. 张扣扣在儿童期(13 岁)经历的母亲被杀害这一重大生活事件,与其所患的偏执性人格障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张扣扣家属曾邀请国内三位权威精神病法医专家进行论证,结论为张扣扣患有急性应激障碍,作案时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然而,一、二审法院均未准许精神病鉴定申请,这一程序瑕疵令人存疑 —— 是否患有精神障碍,应由医学专业判断,而非司法主观决断,这既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也是司法严谨性的体现。 4. 张扣扣因 "为母复仇",被当地一、二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未充分考量案件的历史背景与特殊性。张扣扣的行为虽触犯法律,却根植于早年司法救济的缺失,简单量刑难以回应公众对 "何以至此" 的追问。 5. 审理此案的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曹建国已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2023 年 4 月,陕西省纪委监委通报其 "2013 年至 2020 年收受 8 名私营企业主礼金 18 万余元,长期与多名私营企业主打麻将带彩头",最终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作为参与此案审判的关键司法人员,其违纪违法事实难免让人对案件审理的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 —— 当司法者自身突破底线,如何保证判决的公允? 据公开报道,"张扣扣杀人案" 二审开庭前,围绕是否启动精神病鉴定的争议极大。张扣扣的家人和辩护人已申请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以明确 13 岁时母亲被打死的经历对其作案时的刑事责任能力是否有影响,但一、二审法院均未准许这一请求。在我看来,张扣扣是否有精神病,法律人说了不算,只有医学专家才有发言权。司法机关应满足其家人和辩护人的申请,这样才能给各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无论从法律效果还是社会效果来看,此举都利远大于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表明法律并非冰冷无情,对于故意杀人罪,会根据不同情况判处相应刑罚。对张扣扣从轻处罚,才能让权贵们不敢胡作非为,震慑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犯罪分子,使其不敢肆无忌惮地违法犯罪,更能体现司法的公平正义。当个体无法通过法律获得公平对待时,自然法则便成了最后的正义防线。 这个世界上,除了法律,还有天理人心,还有正义公道!张扣扣亲眼目睹母亲被王家四个男人恃强凌弱当场打死,年幼的他抱着母亲的尸体痛不欲生,还眼睁睁看着母亲的遗体被扒开头皮、锯开头骨当众解剖。若这样的经历都无法激起刻骨的仇恨,那便不是真正的人,只是一具 "遵纪守法" 的行尸走肉! 孔子在《礼记》中教导中华儿女:"对待杀害父母的仇人,要睡在草垫上,枕着盾牌,不做官,与仇人不共戴天。无论在集市还是官府,遇见他就与之决斗,要随身携带兵器,不必回家去取!" 世间之人皆视父母为最至亲至爱,若最亲之人遭恃强凌弱者残害而不复仇,那便连畜生都不如! 武松为兄复仇杀潘金莲前,并非没有走法律途径,只是阳谷县太爷收受西门庆贿赂后一手遮天,即便如武松这般身处体制内的都头,也只能愤而私行复仇。更何况面对仅蹲了四年多监狱就出来横行街市,且从未向张扣扣家赔礼道歉的王家恶霸父子呢! 有位网友提出 "若张扣扣面对母亲遭此残害而不复仇,那便连畜生都不如",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绝大多数网友的认同。可见,老百姓抗议的不是一份不公的法律判决,而是抗议自己被推向连畜生都不如的境地!老百姓维护的并非张扣扣的生命,而是人类最基本的天理人伦! 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注定会像猪狗般任人宰割,这是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一个没有天理的民族,注定会遭天谴,这一点虽未被证实,老百姓也不愿看到它被证实,故而掀起了维护天理的舆论浪潮。说到底,老百姓守护的是中华民族的未来,是中华文明的传承,是 14 亿中国人民的前途! "既然法律无法保护我,我何不自己动手?" 这是世人共有的心理,张扣扣的杀人行为根源便在于此。这不仅是法律问题,也不仅是以暴制暴的社会问题,更关乎人性善恶,以及对正义的定义与维护正义方式的思辨。比如,我们能为抵御外族入侵而合法杀人,那是为正义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壮举;可当同胞杀人却不受惩罚时,受害者难道不能用同样的暴力讨回正义吗?扪心自问,若身处张扣扣的境地,或许我也会不顾生死,用自己的方式夺回属于自己的正义。 若最高人民法院不再审纠正,后果将极为严重,可能引发无数滥杀无辜的类似案件。杀一人是死,杀十人、百人亦是死,这会将张扣扣逼成杨佳、郑永军、胡文海般的人物。司法不公在先,司法失职未能解决问题在后,张扣扣不过是启动了 "自然正义" 模式,何罪之有?即便有罪,也绝不该判死刑!法律的公平,比法律的严苛更具社会约束力。 司法应当有倾听民意的耳朵,在法律允许的自由裁量范围内,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合理的民意应得到尊重,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司法。司法领域的民意,首要特征便是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基于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认知,民意对司法的关注,往往体现在对公平正义的向往上,承载着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期待。司法的本质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这与民意的目的一致,因此从应然层面讲,民意的目标与司法的追求应是统一的。 民意表达是对司法的有力监督,也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需要。监督是一种约束,能制约权力滥用,确保监督目的实现。因司法实现公平正义的本质与民意目的一致,民意监督司法便成为必然。只有通过监督,民意才能知晓司法是否实现了其目的。司法过程是法律适用的过程,民众关心的是立法所体现的民意能否在司法中得以实现。当司法活动置于民意监督之下,审判过程最大限度公开,裁判理由详尽公布,法律文书广泛公开,让司法活动透明化,司法不公便能得到最大程度遏制,司法也必将朝着契合民意的公平正义方向前行。 尽管张扣扣杀害三人,但我并不认为他对社会构成威胁,相反,真正对社会有威胁的是被他所杀的那些仗势欺人之辈。在我看来,张扣扣是集忠孝仁义于一身的悲剧人物:报名参军是为忠,为母复仇是为孝,不杀无辜是为仁,投案自首是为义。这个汉子,在需要法律时,法律转身离去;当他挥刀复仇时,法律却又出现了。我始终坚持 "请刀下留人" 的观点。 司法公正离不开民意参与,司法审判更不能违背人之常情,独立审判与尊重民意并不矛盾。长期以来,在一些热点公共案件中,总有声音指责 "舆论绑架司法"" 民意破坏法治 ",甚至有个别司法人员称" 不看完案卷就评论判决对错,就是耍流氓 "。强调审判独立没错,但试图以" 专业 " 为借口堵住众人之口,是对民意的漠视。任何判决都不应回避民意议论,脱离公众的司法无法赢得公信。司法应尊重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与基本道德诉求,将个案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中综合考量。 或许有人认为轻判张扣扣会引发复仇泛滥,使社会沦为兽性横生的混乱之地。但我认为,若严惩张扣扣,社会才真会陷入混乱:权贵们会更加目无党纪国法,肆无忌惮地欺压百姓,最终导致官逼民反、党失政权、国家动荡。由国家公权力取代个人生杀予夺之权,是人类发展与文明社会的必然。但法律本身也是一种报复制度,只是主体变为国家,且建立在多数人利益之上。人类的复仇欲望难以根除,私仇滋生皆因法律缺失,使坏人未受惩处、正义无法伸张。仅有法律可依远远不够,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才行。要让原始私力救济消失,关键不在于司法限制,而在于司法公正程度。 我深知,复仇必然无休无止,最终比拼的是谁更强,但只信奉强者绝非我们的追求。我们应追问是谁造就了复仇的土壤,暴民并非天生,需从根源解决问题。最理想的状态是人人都有法治自觉,且法治能确保每个案件的公平正义,否则机械司法无法解决问题。若我们真心吸取同态复仇恶性循环的教训,真正理解以暴制暴只会加剧暴力的本质,就应更谦卑、谨慎地运用司法权力,杜绝任何勾兑交易。唯有尽可能实现每个个案的正义,才能建立法治信仰,让公众自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非采取同态复仇这般极端的私力救济方式。只有当法治思维成为每个个体,尤其是司法者的自觉,法治治理体系才能最终建立,法治社会才能得以维系。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我看来,"执法必严" 最为重要。古人云 "不患寡而患不均",可见执法公平至关重要,应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绝不能出现偷自行车者,有人仅拘留十天,有人却判五年有期徒刑的不公现象。因此,张扣扣一案的关键在于,当年对王家人的判罚是否公平。若王家人当年已依当时法律受到应有的、足够的惩处,那案件早已了结,张扣扣便无复仇理由,其如今行为就是彻头彻尾的杀人行径,需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但 —— 我必须强调 —— 若 22 年前,即 1996 年的秋天,王家人凭借势力操控司法,未受应有的惩罚,那么张扣扣如今的行为便充满正义感:他是在替司法发声,完成当年法律未竟之事。他隐忍二十多年,以行动向世人诠释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杀母之仇,无论时隔多久,都需偿还",这是最基本的公平。若连这都做不到,那每个人的母亲都可能被肆意残害。因此,若当年判罚不公,不仅王家三人,就连当年参与办案、徇私枉法之人,都罪该万死。 "不能爱母,何以爱党国?" 山东于欢辱母杀人案虽已落幕,但留给社会的反思远未停止。我们常说祖国是 "母亲",号召百姓爱国、保家卫国。可一个男人若连自己的家都守不住,何谈卫国?若连亲生母亲都护不了,又怎能守护国家这个 "母亲"? 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无缘无故的同情,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支持。张扣扣的行为绝非偶然。若没有有权有势的王家人欺凌,若张母未被王家人打死,若 22 年前杀张母的凶手受到法律应有的严惩,张扣扣会复仇吗?22 年后的这场惨案还会发生吗? 实则,正是当年法律的缺失导致张扣扣如今拔刀杀人;正是法治不公,让他不得不自己寻求公平;正是法律未为张母伸张正义,才迫使张扣扣挥刀替母维权 —— 虽法律已 "死",但儿子尚在!司法腐败与法治缺失的欠账终究要还。陕西汉中的这场惨案注定无法避免,即便在此地避免,也可能在其他地方上演。"法治不明则复仇兴",这是千古不变的规律,但愿我们能引以为戒,不再让类似悲剧重演! 人生在世,有两大仇不可不报: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即便是狗,被踩后也会跳起来反击,何况人呢?若连这都做不到,便真不如狗了。张扣扣的行为充满绿林气息,他追求的是江湖武侠式的 "公平",就像郭靖对郭芙说:"你斩断人家一臂,我也要斩断你一臂。""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 ",这种公平本应由法治赋予张扣扣。 但现实却逼着他迈出了这武侠式的一步。很少有人能体会,十来岁时亲眼目睹母亲被活活打死,且凶手未受法律应有惩处,这种仇恨即便历经十世也难以消解。但张扣扣背负着这般仇恨,仍守住了底线:不伤害女人、孩子及无关人员。他说:"与你们无关,我只杀他们。" 只惩罚那些该死之人。若当年司法不公,那么张扣扣的行为便是一种公正的司法程序。抛开此案,从网络、媒体披露及我们耳闻目睹的现实来看,司法界的贪婪与腐败触目惊心,从民事到刑事案件,难有净土,却还自欺欺人地宣称 "一切都在变好"。当人们都期盼 "佐罗" 式的英雄出现时,法律便成了空谈,司法沦为笑话。不正本清源,仅靠删帖禁言毫无意义。 我知道,复仇必然没完没了,最终看谁能笑到最后,但信奉强者绝非我们的追求。我们应追问是谁造就了复仇的土壤,暴民并非天生,需从根源解决。最理想的是人人都有法治自觉,且法治能确保每个案件的公平正义,否则机械司法无解。若我们真心吸取同态复仇的教训,明白以暴制暴只会加剧暴力,就应更谦卑、谨慎地运用司法权力,杜绝勾兑交易。只有尽可能实现每个个案的正义,才能建立法治信仰,让公众自觉通过法律解决问题,而非采取同态复仇这种极端私力救济。只有当法治思维成为每个个体,尤其是司法者的自觉,法治治理体系才能建成,法治社会才能存续。 如何惩处张扣扣,关乎党国存亡。若判张扣扣有罪,必然失民心。司法就像风向标,会引导社会风气向好或向坏发展。健康的司法惩恶扬善,推动社会风气向好;若司法惩善扬恶,则会导致社会风气败坏。司法不公是社会道德堕落、风气恶化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法律是任何社会都必须具备的底线,且往往是穷者与弱者的保护屏障。若人们不相信法律,穷者、弱者该如何自保?若他们觉得法律成了富者、强者的工具,又会采取何种手段自保?暴力便由此滋生。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愤怒便会蔓延,进而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令人忧心,长此以往,"恨" 字会愈发凸显,社会稳定与安全将无从谈起。好的法律不仅要提供程序正义,还应强大且公平,助力界定公共利益,致力于实现实体正义。 绝不能孤立看待张扣扣案。孤立来看,他连杀三人,手段血腥暴力,判死刑似乎理所当然,血亲复仇也绝非暴力杀人的借口。但张母被害案的判决是否伸张正义,王家权势是否影响司法,王正军是否替人顶罪,这才是张扣扣案的原点。道理很简单,现代社会禁止血亲复仇,正是要用法律代替家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因此,法律必须确保自身公正,否则禁止血亲复仇便毫无意义。司法若不公正,便如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说的 "法不治时代",民众便有理由重拾自然法赋予的复仇之权。 实施自然正义时,人们难以精确把控,要么过度,要么不足,无论哪种,都会转化为高昂的社会成本。张扣扣便是如此,仇家仅杀其母一人,他却杀了王家父子三人,这便是自然正义过度实施的巨大社会成本。但这能怪张扣扣吗?不能,因为有限理性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是自然正义的组成。正因如此,为降低自然正义的社会成本,需要一个能精准 "计算" 正义的公共法官 —— 国家。若国家这个公共法官从不缺席,张扣扣还会制造这般 "手刃三人" 的高昂社会成本吗?答案不言而喻。 鉴于审理原案的南郑县法院判决书存在多处疑点:判决书中列举的七名重要证人里,王富军被张福如、张丽波指认为真凶,而杨桂英被曝实为王氏兄弟之母,其可信度存疑。当年原案的疑点已引发舆论哗然,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应启动复查程序,排查是否存在司法不公。此事关乎司法正义与世道人心,复查必须启动,且要严格彻底,绝不能敷衍了事。 若事实证明,张母被害案的审理完全公正,未满 18 岁的王正军确是凶手,张姐张丽波、张父张福如的指控毫无根据,那张扣扣便是被仇恨冲昏头脑的偏执杀人犯,理应受法律最严厉惩罚,执行死刑也无可厚非。但若复查发现,张母被害案审理存在瑕疵,未实现司法正义,打死张母的并非王正军而是他人,那张扣扣的行为至少应获得一定谅解,可参照前清为父报仇的杨献恒案,对其从轻发落,判处死缓、更轻刑罚甚至当庭释放。 报复性反应是任何生物在自然界生存竞争的基本本能,缺少这种本能的物种终将被淘汰。对他人报复的畏惧,会减少侵犯行为,复仇本能为人类创造了博弈论意义上的 "合作互不侵犯",推动人类走向 "文明"。 复仇本质上是一种延迟的报复。根据现代法律,当场反击、即时报复可能构成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而复仇被现代法律禁止,原因之一是被侵犯者有时间寻求公权力救济,有司法可替代。国家垄断合法暴力,将个人复仇权收归公有,前提是公权力能公正履行职责 —— 若公权力失职,个体的复仇冲动便成了无法遏制的人性本能。 审视当下中国的法律体系,虽条文完备,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存在诸多漏洞与不足。司法不公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案件的处理结果难以令人信服。任何刑事案件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不能仅仅关注案件表面的事实,更要深入剖析案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就张扣扣案而言,他是在杀母凶手未能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父亲多次上访也石沉大海、毫无结果的绝望处境下,才选择了极端的复仇之路。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若能审慎对待此案,或许能对那些有钱有势、肆意妄为的犯罪分子起到震慑作用。当法律无法为公民提供应有的保护时,人们很容易产生 "既然法律靠不住,那我只能自己来捍卫权益" 的想法,张扣扣的杀人行为,归根结底便是源于这样的无奈与愤怒。 这一案件所涉及的,远不止是简单的法律问题,也不仅是以暴制暴的社会现象,其背后还蕴含着深刻的人性善恶探讨,以及对于正义的定义和维护正义的方式的深度思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我们处于张扣扣的境地,亲眼目睹母亲被残忍杀害,而凶手却逍遥法外,内心的仇恨恐怕会如熊熊烈火般燃烧。在这种极端的情绪下,或许很多人都会像张扣扣一样,不惜一切代价,哪怕舍弃生命,也要用自己的方式夺回那份被法律遗忘的正义。 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 在我看来,执法过程中的公平性至关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法律条文本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都应受到法律同等的约束与保护。不能出现同样的违法行为,有权有势者只需受到轻微的惩罚,而普通民众却要承受重罚的情况。就如同偷自行车这样的行为,不能有人只被拘留十天,而另一些人却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这样的差别对待显然是不公平的,也会严重损害法律的公信力。 张扣扣一案的关键核心在于,当年对王家人的判罚是否公正合理。如果王家人在当年的案件中,确实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受到了应有的惩处,量刑恰当,那么这起案件在当时就应该画上句号,张扣扣也就没有理由在多年后实施复仇行为。他如今的所作所为,就纯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犯行径,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但是,倘若 22 年前,也就是 1996 年那个令人痛心的秋天,王家人凭借自身的势力干预司法,使得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失公正,他们根本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张扣扣今天的行为,便有了另一番解读。他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替司法发声,是在完成当年法律未能完成的使命。他在漫长的岁月里默默隐忍了二十年,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诠释了什么叫做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杀母之仇,不共戴天",在他心中,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平原则。如果当年的判罚存在不公,那么不仅是王家三人,那些当年参与办案、徇私枉法的人员,都应该受到应有的惩处。张扣扣的行为,充满了江湖绿林好汉般的侠义气息,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江湖武侠式的 "公平",就如同郭靖对郭芙所说的:"你斩断人家一臂,我也要斩断你一臂。"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本是天经地义的道理,这种公平,本应由法治来给予张扣扣。然而,现实却如此残酷,在法律无法为他主持公道的情况下,他被迫迈出了这充满悲壮色彩的 "武侠一步"。 相信很少有人能体会那种在十来岁的年纪,亲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而凶手却逃脱法律制裁的痛苦与仇恨。这种仇恨,犹如一颗毒瘤,在张扣扣的心中生根发芽,恐怕历经十辈子也难以消除。但即便背负着如此深仇大恨,张扣扣在实施复仇行动时,依然守住了自己的底线,他没有对无辜的女人和孩子下手,只针对与当年案件相关的人员。他明确表示:"与你们无关,我只杀他们。" 如果当年的司法确实存在不公,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扣扣的行为就像是一种自行启动的公正司法程序。更何况,当前仍有不少地方的政法机关存在将上访行为当作犯罪处理的情况,将上访人员抓回去拘留判刑。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张扣扣不自己采取行动惩处罪犯,那些违纪犯法的人又怎么可能得到法律的制裁呢? 所以,我始终坚持认为,在当前法治还未能完全深入人心真正实行、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时候,张扣扣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那些权贵们起到了震慑作用,让他们不敢再肆无忌惮地仗势欺人、胡作非为。审慎处理张扣扣案,或许能够避免未来出现更多因绝望而报复社会、滥杀无辜的 "张扣扣"。只有让公众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才能真正筑牢社会稳定的根基。或许有人会担忧,轻判张扣扣会引发复仇之风的泛滥,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仿佛人类将退回到野蛮的时代。但我却认为,倘若忽视案件根源的不公而严惩张扣扣,社会才真的有可能陷入混乱。权贵们会更加无视党纪国法,变本加厉地欺压百姓,最终可能引发官逼民反的严重后果,导致党失去政权,国家陷入动荡。 从本质上来说,法律也是一种报复制度,只不过它将报复的主体从个人转变为国家,并且是建立在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基础之上。人类内心深处的复仇愿望是难以彻底消除的,私仇的产生,往往是因为法律的缺失,使得坏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正义无法得到伸张。要想彻底杜绝原始的私力救济行为,关键不在于限制人们的行动,而在于提高司法的公正程度。只有让人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能够为他们主持公道,他们才会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目前,部分地方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存在对法律随意解读、任性判决的现象。这导致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得不反复申诉,信访局人满为患。这种情况使得一些走投无路、状告无门的人,无奈之下选择自行执法,甚至做出自杀性报复社会、滥杀无辜的极端行为。司法,本应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最高人民法院无疑是这道防线的终极守护者,它与人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在当前只有上级机关才能管得了下级机关的体制下,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尤为重要,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应当直接进行审判,绝不能犯官僚主义错误,将案件发回当地重审。因为让当地法院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判决,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违背了人性的弱点。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审判上诉和申诉案件,起初可能会面临较大的工作量,但从长远来看,只要能够坚持公正审判,并严格追究相关责任,地方法院的法官就会有所忌惮,不敢再肆意妄为地进行不公正审判。当地方司法公正得以保障,上诉和申诉的案件自然就会减少。 司法不公所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还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动摇了人们对法治的信仰。我们必须努力营造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当人们与他人发生纠纷时,能够自然而然地想到借助公权力的介入来解决问题,并且能够高效、便捷地实现自己的诉求。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公权力的公信力,避免出现人们因绝望而自行执法,甚至报复社会的悲剧。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公权力若不能为人民主持公道,人民就必然会寻找自己的方式来讨回公道。清朝末年,司法腐败横行,百姓冤屈无处申诉,最终导致民心尽失,这便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党必须加强对司法的全面统一领导,对于司法机关不公正的裁决,要及时进行督促和纠正,致力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的独立办案演变成不受约束的 "独立王国",对于那些违法执法、贪赃枉法的司法工作人员,必须依法严惩,绝不姑息。 司法的意义,不仅在于惩罚犯罪,更在于修复正义。若 22 年前的案件确属公正,王正军系真凶且量刑适当,张扣扣便应受法律严惩;但若复查发现司法瑕疵,甚至存在徇私枉法,就应正视 "当年法律欠张扣扣一家一个公道" 的事实。此时对张扣扣从轻处罚,绝非否定法律,而是以个案推动法治完善 —— 让公众相信,司法既能惩罚犯罪,也能纠正过错。 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再审,既是对个案正义的负责,更是对法治信仰的守护。司法不应回避民意,更不能脱离 "人之常情"—— 独立审判与尊重民意并不矛盾,正如于欢案所展现的,民意推动的不是 "舆论绑架司法",而是 "司法回归公正"。一个案件的判决,从来都不只是对当事人的裁决,更是对社会价值的指引:是鼓励公民相信法律,还是逼迫他们选择极端? "法治不明则复仇兴",这是千古定律。张扣扣案已超越个案范畴,成为检验司法是否兼顾天理、国法、人情的试金石。吁请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再审,不是为张扣扣的行为辩护,而是为了让每个公民相信:当至亲受辱、权利受损时,法律不会缺席;当司法出现偏差时,正义终会纠正。这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模样 —— 既不让私刑有存在的必要,也不让公正有迟到的借口。 在司法日益公开公正的大背景下,只要案件证据充分、事实清楚,就始终存在翻案的希望,但这需要给予律师足够的时间和信任。以聂树斌案为例,其平反过程堪称艰难。由于涉案人员众多、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每深入调查一步,都会遭遇数倍的阻力。即便如此,警察郑成月仍为该案奔走11年,不仅自掏腰包支持聂树斌的父母寻求法律帮助,还鼓励他们坚持上诉;聂树斌的母亲更是怀揣着对儿子的爱与对正义的信念,执着上诉21年,最终为儿子洗清了冤屈。 我吁请最高的人民法院,对张扣扣案启动再审。这也许是许多人眼中 "不可能的事情"—— 面对沉疴已久的司法积弊,面对牵动无数人心的复杂个案,再审纠错仿佛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毕竟,二十余年的时光足以让证据蒙尘,足以让记忆模糊,更足以让既成的司法结论沉淀为难以撼动的 "铁案"。有人会说,张扣扣案早已尘埃落定,翻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与其寄望于渺茫的再审,不如接受现实的无奈。 但每当我想起我们北京中公法律师事务所去前年代理的曹某彬案,便觉得希望从未真正熄灭。那起案件中[(2004)萧刑初字笫80号],曹某彬因被诬告陷害(犯强制猥亵妇女罪),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度过了二十一个春秋。从血气方刚的青年到两鬓染霜的中年,他在日复一日的申诉中耗尽了青春,家人也因这桩冤案备受牵连,生活在旁人的指点与非议之中。二十一年里,他写过的申诉材料和走访过的司法机关不计其数,却一次次在 "证据不足"" 维持原判 "的回复中陷入绝望。当时所有人都劝他放弃,说" 胳膊拧不过大腿 ",说" 这世道本就如此 "。 可我们北京中公法律师事务所重大疑难案件部的律师团队接手案件后,没有被 "陈年旧案" 的标签吓退。谁也没有想到,这起被认为 "永无翻身之日" 的冤案,最终得到纠正,我们深刻体会到,所谓的 "不可能",往往只是 "尚未被实现" 的代名词。 司法的长河中,或许有淤塞与停滞,但从未真正断绝过奔涌向前的力量。曹某彬案的平反,恰如暗夜中的一盏灯,它告诉我们:哪怕时间再久,哪怕阻力再大,只要证据确凿,只要法理昭然,只要有人坚持为正义奔走,沉冤便有昭雪的可能。张扣扣案的再审之路或许同样布满荆棘,但只要我们相信,法治的进步从不因个案的艰难而止步,相信每个坚守公正的努力都在为未来积蓄力量,那束属于正义的光,就终会穿透云层,照亮前行的路。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