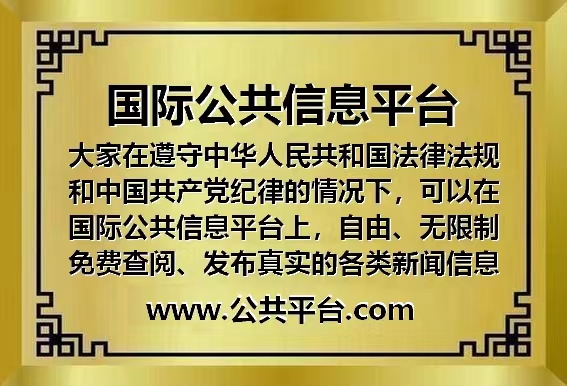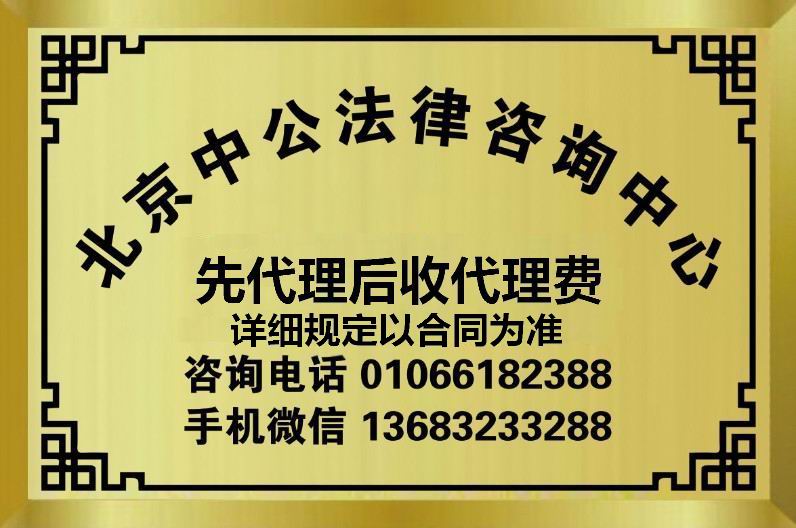|
|
陈中华:彻查山西大同的订婚强奸案,法律不容恶意控告敲诈勒索
近期司法实践中,如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江西南昌“女上位强奸案”等案件引发公众关注。这些案件的核心争议不仅在于“是否违背妇女意志”这一法律事实判断,更涉及背后是否存在以“刑事指控”为手段的恶意敲诈行为。
从法律层面看,“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的核心构成要件,需以发生性关系时女方的真实意愿为判断标准。但部分案件中,女方在双方存在恋爱关系、准婚姻关系(如订婚)等前提下,事后以“不同意”为由提起强奸指控,其动机可能指向经济利益——例如以“指控强奸”胁迫男方增加彩礼、补偿款等。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将司法程序作为勒索工具,不仅可能损害男方权益,也会对司法公信力造成负面影响。
值得思考的是,此类案件反映出更深层的社会价值冲突:一方面,法律必须坚决保护妇女的性自主权,杜绝任何形式的强迫性行为;另一方面,若对“事后反告”的动机缺乏审查,可能导致司法资源被滥用,甚至形成“以告施压”的不良导向。例如,有观点指出,若女方可随意以“不同意”为由指控,可能迫使男方在亲密关系中时刻保留录音、监控等证据,这不仅违背人际关系的信任基础,也会对社会行为模式产生扭曲指引。
从法律功能角度,刑法除了惩罚犯罪、保护受害人外,还承担着价值引导作用。对于以“强奸指控”实施敲诈的行为,现行法律中敲诈勒索罪虽可适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指控动机”与“勒索目的”的关联性,仍需更明确的规则或司法解释。例如,是否应建立对“事后指控”的背景审查机制,对存在明显经济利益纠葛的案件进行重点核实,避免“诬告”与“真实维权”的界限模糊化。
山西大同案二审判决已尘埃落定并入选最高院案例库,但此类案件引发的争议仍值得深思:法律如何在保护个体权利与防止权利滥用之间寻求平衡?当“性自主权”与“恶意诉讼”可能交织时,司法机关是否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如证据审查标准、诬告追责机制等)进行更精准的规范?这不仅关乎个案公正,更涉及社会对“权利行使”与“法律诚信”的价值认知塑造。
制度完善的核心在于平衡权利保护与司法公正:
• 一方面,需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同意”的认定标准,避免“关系背景”被误读为“默示许可”;
• 另一方面,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女方恶意控告、勒索财物的,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防止司法程序被滥用。
此类案件的社会价值争议,本质是法律对“真实意志”与“行为动机”的界定难题。法律既要坚决保护公民免受性侵害,也要避免让“权利主张”异化为利益博弈的工具。最终,司法裁判的意义不仅在于个案定性,更在于向社会明确:任何关系中的性行为,都应以双方真实、自愿的同意为前提,而恶意利用法律程序谋取私利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规制。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