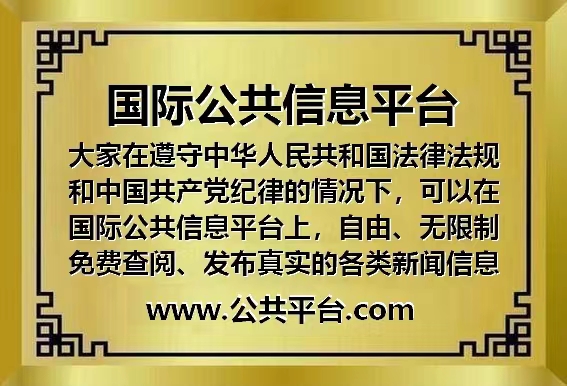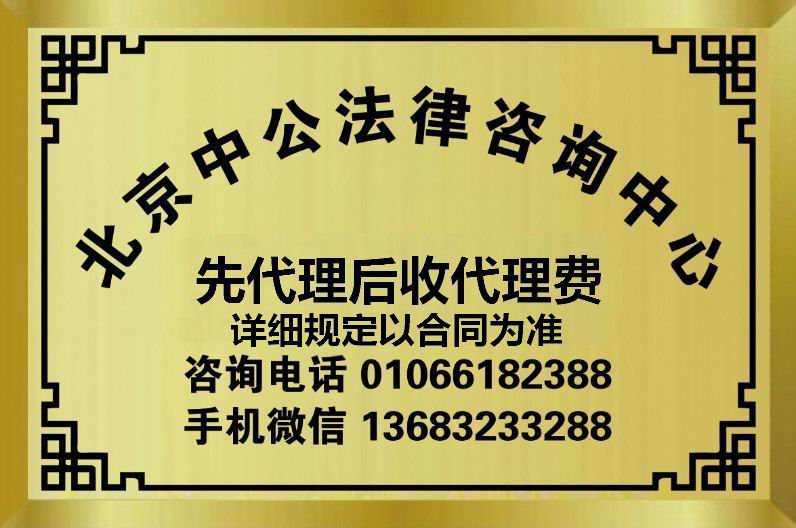|
|
陈中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司法腐败,才能让法庭回归讲理的本质
2021年,60岁的姚辉,2003年至2016年4月任深圳中院刑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2016年至2017年,任深圳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2017年10月退休。在退休近4年后,姚辉被查。2021年5月21日,深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深圳市监察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消息:姚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司法文书采信的证据显示,姚辉多次向经办法官打招呼,过问案件,甚至直接指令经办法官按照其指示行事,为涉案被告人从轻处罚。在姚辉退休之后,其通过自身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采用电话询问、请客吃饭等方式,向经办法官、检察官打听案情,表达请托事项。据悉,这些请托的案件包括受贿案、走私普通货物案、贪污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合同诈骗案、行贿案、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案、挪用资金案、职务侵占案等。请托人以律师居多,也有企业负责人、深圳市检察官和纪委人员等。 在姚辉案中,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共有28笔,其接受的贿赂款项中有15笔来自律师或律所工作人员。这些请托人找到姚辉,多是希望利用姚辉原职权及地位形成的便利,或由姚辉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在刑事案件审理中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数是希望所请托的案件能够从轻处罚、尽快审结等。裁判文书显示,有的律师向姚辉明确表示,如果能在姚辉的帮忙下争取对被告人从轻判处,就能全额拿下高额风险代理费用。有的律师则在了解到案件从轻判处没有空间时,仍愿意送钱给姚辉。 裁判文书显示,2015年,广东守静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某炽代理某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杜言受贿案,2016年案件在深圳中院审理时,姚辉为主审法官和审判长。林某炽曾约见姚辉,与其沟通杜某案的基本情况,同时询问该案是否有从轻处罚的空间。姚辉表示,该案因案件影响比较大,关注度高,量刑方面估计没有什么空间。对此,林某炽表示明白,又请求姚辉,希望能让他在法庭上充分发表辩护意见,不要打断他的发言,姚辉答应下来。 随后,在杜某案庭审时,按照林某炽的要求,姚辉给了他充分的时间发表辩护意见,“没有打断我的发言。”林某炽事后供称。杜某案判决后,林某炽送给姚辉20万元。裁判文书显示,林某炽送钱的目的,一是因为姚辉在庭审时关照了他,二是和他搞好关系,方便在以后案件上给他提供关照。公开资料显示,林某炽曾任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2013年曾被聘为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咨询专家。 裁判文书显示,2015年,姚辉接受广东金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某泉请托,在审理范某命受贿案提供帮助,收受张某泉贿送50万元,但后来发现案情比较复杂,于是退回40万元。2017年10月,姚辉退休离职,但仍接受请托人请托,利用其职权及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直至2021年5月被立案调查。 一、案件核心事实与细节 1. 权力寻租链条: ◦ 姚辉在2003年至2017年任职期间(含退休后),利用职务影响力干预10余类案件(涵盖受贿、走私、贪污、合同诈骗等),通过“打招呼”“指令办案”等方式为被告人谋取从轻处罚,甚至退休后仍以电话询问、请客吃饭等方式干预司法。 ◦ 受贿犯罪共28笔,其中14位律师为谋取庭审便利、案件关照等向其行贿,金额从10万元至300万元不等。典型案例包括: ◦ 律师林某炽为“庭审发言不被打断”送20万元,最终获法官“充分发表意见”的“关照”; ◦ 律师武险峰(已判刑)行贿300万元,成为单笔受贿金额最高者; ◦ 多名律师以“红包”“顾问费”等名义长期输送利益,形成“司法掮客”网络。 2. 制度性讽刺: ◦ 2018年最高法与司法部已明确规定“法官不得无故打断律师发言”,而本案中律师却需通过行贿换取这一基本权利,暴露出制度执行与现实的割裂。 二、案件本质与危害 1. 司法公信力的致命伤: ◦ 法庭本应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公正场域,但金钱介入使审判沦为权力交易的筹码。如姚辉直接指令经办法官“按指示行事”,将刑事案件裁判变成个人牟利工具,严重破坏罪刑法定原则。 ◦ 律师本应是法律秩序的维护者,却成为腐蚀司法的“帮凶”。14名律师的行贿行为,折射出部分法律从业者背离职业伦理,将辩护权异化为“金钱开路”的投机工具。 2. 系统性腐败的警示: ◦ 姚辉案横跨任职期与退休期,受贿时间线长、涉及罪名广,且受贿对象包括检察官、纪委人员等,反映出司法腐败可能渗透到权力监督体系内部,形成“利益共同体”。 ◦ 判决书中仅1名律师被追责,其余行贿律师仍“未受刑事处罚”,凸显对“围猎者”的惩治力度不足,可能导致“罚不责众”的侥幸心理。 三、根治路径与深层反思 1. 制度防线需“带电”: ◦ 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对“打招呼”“批条子”等行为全程留痕、终身追责,切断权力干预司法的通道。 ◦ 加强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管,建立“行贿律师黑名单”制度,对违规者依法吊销执业证并追究刑事责任,斩断“金钱—权力”输送链条。 2. 监督体系需“立体”: ◦ 强化司法公开,通过庭审直播、裁判文书上网等方式,将审判权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压缩暗箱操作空间。 ◦ 推动法官与律师“亲清关系”制度化,明确禁止性交往边界(如禁止私下接触、禁止利益输送),建立定期轮岗、回避制度,减少长期任职形成的“圈子文化”。 3. 职业伦理需“重塑”: ◦ 对法官队伍加强廉政教育,将“司法公正”纳入绩效考核核心指标,对违纪者实行“一票否决”; ◦ 律师行业应强化职业道德培训,通过典型案例警示、行业自律检查等方式,引导从业者以专业能力而非“关系运作”赢得案件。 姚辉案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一面映照司法腐败病灶的镜子。当“律师为发言权行贿”成为现实,当“法官靠权力变现”成为路径,法律的天平必然倾斜。唯有以“零容忍”态度惩治司法腐败,以“全链条”思维完善监督机制,才能让法庭回归“讲理”的本质,让正义真正“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不仅是对个案的反思,更是对法治信仰的捍卫。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