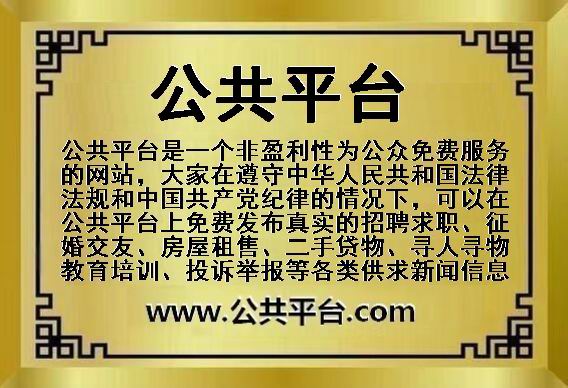|
|
陈中华:国家赔偿金不能仅仅赔工资,含冤者的一切损失都应赔偿
在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国家赔偿制度是纠正公权力过错、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屏障。然而,近期两起国家赔偿案例的曝光,却让这道屏障的 “防护漏洞” 浮出水面 —— 民企老板范海生被错关 212 天仅获赔 15 万余元,不及律师费一半;谷建彬因阻强拆被羁押 295 天获赔 21 万,却要面对 3000 多万元的贷款压力。这些案例尖锐地揭示出一个核心问题:当前国家赔偿以 “工资补偿” 为核心的模式,远远无法覆盖含冤者承受的全方位、深层次损失。国家赔偿不能仅仅停留在 “赔工资” 的层面,含冤者的财产损耗、职业毁灭、精神创伤、社会关系断裂等一切损失,都理应得到全面赔付;更重要的是,国家赔偿金不应由全体纳税人 “埋单”,而需追溯至违法办案的司法人员,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筑牢司法公正的防线,还给含冤者一个完整的人生。 一、赔偿 “缩水”:含冤者的损失远不止 “失去的工资” 从范海生的遭遇来看,这场持续数年的冤屈,对他而言绝非 “212 天自由” 与 “15 万赔偿” 的简单换算。作为北京中科普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被错误羁押期间,公司的正常经营陷入停滞:与浙江、广东等地多家合作企业的合作终止,不仅直接损失了巨额收益,更错失了长期积累的商业信誉与市场机会;更致命的是,公司原本作为某重大国际赛事抗菌餐具供应商的资格,也因这场冤案化为泡影 —— 这种级别的商业合作,一旦错失,几乎没有挽回的可能,背后是企业未来数年的发展潜力被彻底扼杀。然而,在法院的赔偿决定中,这些实实在在的财产损失被完全忽略,仅以 “人身自由赔偿金 + 少量精神损害抚慰金” 草草结案。范海生那句 “国家赔偿不到律师费的一半”,道尽了含冤者在维权路上的无奈与荒诞 —— 为了洗清冤屈,他付出的成本早已远超所谓的 “赔偿”,而这场冤案对他事业造成的毁灭性打击,更是 15 万元难以衡量的。 谷建彬的经历则更添悲情色彩。曾经,他的 1.5 万平方米猪场生意红火,一年能赚上千万元,是家庭生计的支柱;如今,猪场被强拆后只剩断壁残垣,他因 “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 被羁押 295 天,即便最终获得 21 万元国家赔偿,在 3000 多万元的贷款面前,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为了维持生计,他连每天 2 万元的饲料都快供不上;怕查出病没钱治,他不敢去医院做检查;甚至连律师费都还欠着,唯一的指望竟是迟迟未落实的拆迁补偿。对谷建彬而言,国家赔偿的 21 万元,既无法弥补猪场被强拆的财产损失,也无法偿还因冤案导致的债务危机,更无法修复他因冤屈而断裂的生活轨迹。他失去的不仅是 295 天的自由,更是曾经安稳的生活、对未来的期待,以及一个普通人应有的尊严。 这两起案例并非个例,赵作海的悲剧更是将国家赔偿制度的短板暴露无遗。11 年的牢狱生涯,让他与社会彻底脱节 —— 出狱后连手机都不会使用,社会化过程的断裂使他难以融入正常生活;65 万元的赔偿款,在人情纠葛与骗局中迅速耗尽,最终他在孤独与病痛中离世。11 年里,他失去的何止是 “工资”?是职业生命的彻底终结(出狱后已无劳动能力与职业技能),是亲情友情的疏离(长期羁押让社会关系逐渐瓦解),是身心健康的永久创伤(脑梗、高血压等疾病缠身,却因对西药的抗拒而延误治疗)。以 “工资标准” 计算的赔偿,根本无法填补这种系统性的人生损害。正如赵作海的遭遇所揭示的:含冤者的损失是 “全维度” 的,从物质到精神,从当下到未来,从个人到家庭,每一个层面都被冤案深深刺痛。现行国家赔偿制度若只盯着 “人身自由” 这一项,忽略了财产、职业、精神、社会关系等其他损失,本质上就是对正义的 “打折”,是对含冤者权利的二次伤害。 二、责任错位:国家赔偿不应让全体纳税人 “背锅” 当前国家赔偿制度的另一大痛点,在于责任主体的错位 —— 无论司法人员是否存在违法或渎职行为,国家赔偿金最终都由财政买单,也就是全体纳税人共同承担。这种模式看似 “维护了国家形象”,实则掩盖了司法腐败的真相,稀释了违法办案人员的责任,最终导致冤假错案的预防机制形同虚设。 国家赔偿应由违法个人全部承担,警察、检察官、法官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其执法、司法行为代表的是国家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违法过错也应由国家(即全体纳税人)“兜底”。如果司法人员因故意违法(如徇私枉法、收受贿赂)或重大过失(如玩忽职守、证据不足仍强行定罪)导致冤假错案,那么他们就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非让无辜的纳税人承担后果。例如,在范海生案中,律师多次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检察院却以 “不认罪” 为由继续羁押;在谷建彬案中,强拆行为已被确认违法,他的维权行为却被认定为 “破坏生产经营罪”—— 这些环节中,司法人员的决策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况?如果存在,那么国家在对含冤者进行赔偿后,理应向这些违法办案人员全额追偿,让他们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而非将成本转嫁给全体国民。 这种责任追偿机制的缺失,会直接导致司法人员的 “违法成本过低”。当错案的代价由公共资金承担时,部分司法人员可能会放松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反正办错案也不用自己赔钱,只要不被追究刑事责任,最多只是纪律处分。这种心态无疑会助长司法腐败的滋生,让冤假错案的风险持续攀升。相反,如果建立 “先赔偿、后追偿” 的机制 —— 即先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对含冤者进行足额赔偿,再依法向违法办案的司法人员全额追偿,同时对故意违法或重大过失者予以严惩(如吊销执业资格、追究刑事责任等),就能从根本上提高司法人员的违法成本。这不仅是对违法者的惩戒,更是对潜在违法人员的震慑,让每一位司法人员在行使权力时都心存敬畏,不敢逾越法律的红线。 司法腐败是对国家、党和人民危害最严重的腐败形式。它所侵蚀的不仅是经济利益,更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甚至是生命权。部分司法人员为了谋取私利,不惜制造冤假错案,让无辜者身陷囹圄,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更会摧毁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动摇民众对法治的信仰。而让全体纳税人承担国家赔偿的成本,本质上是让无辜者为司法腐败 “买单”,这既不公平,也不利于从源头遏制司法腐败。只有将赔偿责任与违法司法人员直接挂钩,才能让司法队伍真正做到 “权责对等”,让司法权回归公正、透明的轨道。 三、全损赔付:让国家赔偿真正修复受损的人生 国家赔偿的本质,是对公权力过错的救赎,是对含冤者权利的修复。因此,国家赔偿必须实现 “全损赔付”,覆盖含冤者的一切损失,让正义不再留有缺口。 首先,立法层面需扩大赔偿范围,打破 “以工资为核心” 的局限。现行《国家赔偿法》虽规定了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但对财产损失的界定过于狭窄(仅承认 “直接损失”,且对 “直接损失” 的解释过于严格),对职业发展损失、社会关系修复成本、长期医疗康复费用等则完全未提及。未来,应将含冤者因冤案导致的商业信誉损失、市场机会损失、职业技能退化的培训费用、家庭关系修复的必要支出、长期心理治疗与生理康复费用等,均纳入赔偿范围。例如,对范海生这样的企业家,应赔偿其企业因冤案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商业合作终止的预期收益损失;对赵作海这样长期羁押者,应赔偿其出狱后的社会化培训费用、长期医疗费用等。只有让赔偿范围与含冤者的实际损失相匹配,才能真正实现 “填补损害” 的制度初衷。 其次,需细化精神损害赔偿标准,避免 “象征性补偿”。当前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确定缺乏明确标准,实践中往往 “一刀切”—— 无论冤屈持续多久、损害多严重,抚慰金数额都相对固定(如范海生 212 天获赔 5 万,谷建彬 295 天获赔数额也与之相近)。这种做法完全忽视了精神损害的个体差异:15 年冤狱(如张志超案)与 1 年冤狱,对当事人精神的打击程度天差地别;企业家因冤案失去事业与普通人因冤案失去工作,其精神痛苦的来源与深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应建立 “精神损害程度评估体系”,综合考虑羁押时长、冤屈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当事人的心理创伤程度等因素,制定差异化的赔偿标准,让精神损害赔偿真正与损害程度挂钩,而非沦为 “安慰性” 的象征。 最后,必须强化司法公正的制度保障,从源头减少冤假错案。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兴衰存亡,这是被历史反复验证的真理。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与英军激战,岸边民众却冷漠围观甚至喝彩;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部分民众甚至协助外敌 —— 这种 “民心背离” 的背后,除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更与长期的文字狱、猖獗的司法腐败密切相关。当民众在司法中感受不到公平正义,对政权的认同感便会逐渐瓦解。如今,我们更应警惕司法不公的危害:党必须加强对司法机关的全面、绝对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主办案沦为 “独立王国”;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依法严惩,绝不姑息。只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筑牢党执政的民心根基,让社会稳定发展。 从范海生的申诉,到谷建彬的无助,再到赵作海的悲剧,这些案例都在呼唤一个更完善、更公正的国家赔偿制度。国家赔偿不应只是 “赔工资”,而应是 “全损赔付”;不应由全体纳税人 “埋单”,而应让违法者担责。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修复含冤者受损的人生,才能让正义不再打折,才能让法治的光芒照亮每一个角落。这不仅是对个体权利的尊重,更是法治文明进阶的必由之路。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