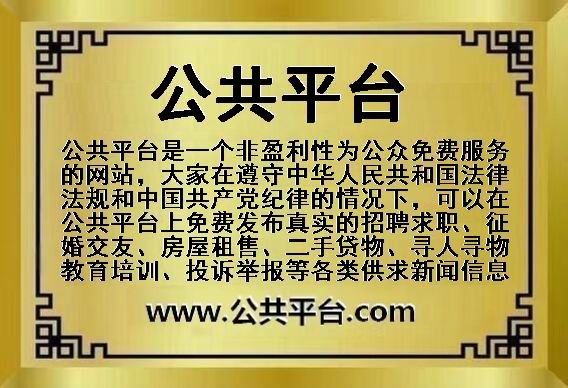|
|
陈中华:公务员要从乡长被农民活埋、派出所长被打死中汲取教训
1999年江西丰城“活埋乡长”事件,是我国基层治理史上一道浸满血泪的伤痕。这起悲剧不仅导致乡长、派出所长等公职人员非正常死亡,更以极端形式撕开了当时基层“漠视民生、滥用权力”的沉疴:一位普通农民因不堪当地政府层层加码的不合理收费,自发收集中央与江西省委“减轻农民负担”的红头文件,试图以合法途径维护权益,却被乡政府以“学习班”名义带走后非正常死亡。家属与亲友50余人前往乡政府“讨说法”,又遭蛮横驱散——正是这种对群众生命尊严的践踏、对合理诉求的无视,彻底点燃了积压已久的民怨。最终,丰城附近四个乡镇数万农民自发携带农具包围乡政府,捣毁办公大楼,乡长被从二楼扔下摔伤后遭活埋,派出所长与一名民警当场被打死,派出所长的尸体甚至被吊在树上示众。这场冲突从不是农民“暴烈”,而是权力傲慢将民生矛盾逼至绝境的必然结果,是基层治理“失能”与“失责”共同催生的苦果,即便时隔二十余年,仍像一面明镜,映照出每一位公务员必须正视的核心命题:权力背离人民意志时,终将付出不可挽回的代价。 事件后续的连锁反应,更凸显了“正视问题、及时纠错”的治理价值。事件发生当夜,江西省政府紧急抽调大批警力进驻丰城平息事态;8月31日,国务院罕见召开全国乡镇党政正职全员紧急电视电话会议,通报多起因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并严令全国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各类款项。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这起事件成为推动我国农业税改革的关键转折点——2006年1月1日,国家正式全面免除农业税,终结了延续两千余年的“皇粮国税”,让亿万农民卸下了沉重负担。从“流血冲突”到“政策革新”的历程清晰警示所有公务员:民生问题从来没有“小事”,任何对群众利益的漠视、对政策执行的扭曲,最终都会累积成破坏社会稳定的“炸药包”;唯有主动倾听诉求、及时化解矛盾,才能守住治理的底线。 若将视野拉得更远,丰城悲剧的教训并非孤例,而是中国历史上“民生与统治”关系的当代映射。中国历史恰似一部“轻徭薄赋则兴,苛捐杂税则亡”的周期性循环史:新王朝建立初期,往往因吸取前朝灭亡教训而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如汉初“十五税一”“三十税一”的轻赋举措,激活民力、奠定“文景之治”根基;北魏均田制、唐代租庸调制也在短期内减轻民负、推动发展。但王朝后期,多因苛捐杂税日益繁重、民生被压榨至极限,最终走向覆灭。《汉书·食货志》中,董仲舒对秦代赋役的记载触目惊心:“古者税民不过什一,至秦则不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秦代赋役较前代激增20-30倍,农民需缴纳五成地租,最终“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成为强秦短命的重要诱因。即便后世有明代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亩等改革,仍难逃“王朝后期赋税膨胀”的循环;民国末期更出现“自古未闻粪有捐,而今唯独屁无税”的荒诞景象,最终因民不聊生加速政权崩塌。历史反复证明:“民富则国强,民穷则国危”,赋税与民生负担的合理性,直接维系社会稳定根基,任何时代的治理者都需敬畏这一铁律。 而在当代,民生负担的核心已从“农业税”转向与企业、职工息息相关的社会保障领域,中央一直要求减轻企业负担——从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推进,到对乱收费、乱罚款的专项整治,再到鼓励地方探索灵活的惠企举措,顶层设计始终围绕“为市场主体松绑、为企业发展赋能”展开。尤其在新冠疫情导致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企业与职工普遍面临收入缩水、经营承压的困境,此时更应遵循中央“减负纾困”导向,暂缓或放缓社保基数上调节奏,而非逆势增加民生与企业负担。但从地方实践来看,部分政策执行与中央要求仍存在偏差,北京市近年来企业职工五险缴费基数的调整,便成为观察这一矛盾的重要窗口。为更清晰呈现政策变化、民生影响及涨率数据,现将2020-2025年北京市企业职工五险缴费基数关键信息整理如下: 执行时间 缴费基数上限(元/月) 缴费基数下限(元/月) 2020年 2654-3613(元/月) 2022年31884-5869 (元/月) 2023年33891-6326 (元/月) 2025年 35811-7162 (元/月) 从数据可见,北京社保基数的持续上涨(尤其是下限近五年累计涨率超98%),与中央“减轻企业负担”的要求、新冠疫情经济下行期企业与职工的实际承压形成鲜明反差:2025年全国已有26个省份暂缓公布社保基数新标准,河北甚至罕见下调,背后正是对“疫情纾困、共渡难关”政策的积极响应——制造业面临原材料涨价与订单流失的双重挤压,服务业尚未完全走出疫情阴影,社保支出的每一分增长,都可能成为压垮小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对职工而言,基数上调直接意味着到手收入缩水:7162元的下限对月薪数千元的低收入群体来说,每月多缴的社保费用可能直接影响房贷还款或日常生计;更值得关注的是,社平工资统计中包含的国企、外企高收入群体,拉高了整体水平,使得私企职工实际收入远低于统计值,却要按偏高基数缴费,形成“被平均”后的缴费压力,这种不公在疫情后经济恢复期更易放大民生焦虑,也与中央“让政策红利真正惠及市场主体和普通民众”的导向相悖。 叠加2025年9月1日生效的“社保强制缴纳”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强调任何规避社保的用工协议均无效)与《住房租赁条例》引发的“房东税”讨论,民生领域的争议更显复杂。在社保强制缴纳层面,官方与民间呈现“善意”与疑虑的碰撞:《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提出,强制社保的核心是保护此前常被拒缴社保的农民工群体,是“老有所养”的保障,农村养老金低的问题需经济发展逐步解决,不应否定社保体系进步;《人民日报》则澄清,“全民强制社保”是自媒体误导——社保缴纳本就具有强制性,此次司法解释仅是统一司法标准,针对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且社保是个人“生存底线”、企业“未来入场券”、国家“社会稳定器”。但质疑声仍未停歇:新冠疫情后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强制缴纳是否与“减轻企业负担”的要求脱节?小微企业如何承受合规成本与基数上涨(近五年下限累计涨超98%)的“双重压力”?在“房东税”争议层面,《住房租赁条例》要求的租房备案与税务信息共享,虽被官方澄清“不新增税收”,却仍引发民众对“隐性税负显性化”的担忧——现实中房东主动报税者极少,税款多转嫁给租客,备案机制让租房成本上升的焦虑被进一步放大,这也与中央“保障民生、稳定消费”的部署存在落差。 这些争议的本质,是部分地方政策执行与中央要求的偏差,是疫情后经济下行期民众对“税负感”的敏感,更是对政策公平性、透明度的诉求。遗憾的是,部分公务员仍依赖“倒逼机制”:发现下属失职、民生问题萌芽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非要等到事故酿成、舆论发酵才被动整改,既违背了中央“主动作为、精准施策”的要求,也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种“等出事后再改正”的逻辑,是责任意识的缺失——用群众痛苦、社会代价“倒逼”工作,与现代治理“防患于未然”的理念背道而驰,更与中央“从源头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治理导向不符。要知道,公务员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岗位责任从不是“被动应对危机”,而是“主动落实中央政策、解决群众难题”;从不是“悲剧后补救”,而是“萌芽时化解”。 历史与现实已给出明确答案:公务员当以丰城悲剧为戒,以中央“减轻企业负担、保障民生”的要求为标尺,尤其要考虑新冠疫情经济下行的实际情况,从民生争议中读懂治理的核心。面对企业经营困境,要主动探索“差异化社保缴费机制”,借鉴浙江用老数据定基数、福建降低企业基数的创新,将中央的惠企政策落到实处;听到职工缴费焦虑,要优化社平工资统计口径,避免“被平均”带来的不公,让政策更贴近民众实际;面对租房税收担忧,要明确规则、消除模糊地带,杜绝“隐性负担”,呼应中央“稳定民生预期”的部署;更要从秦代、民国的教训中敬畏规律,斩断“乱收费、乱罚款”的根源——严格落实中央“规范地方债务管理”的要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弥补财力缺口;地方政府回归公共服务本位,摒弃“卖地生财”“以罚代支”,坚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每一项决策都与中央要求同频、与群众期待共振。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从丰城农民的怒火到社保缴费的焦虑,从秦代的“赋役三十倍于古”到民国的“粪捐之耻”,从中央“减轻企业负担”的明确要求到地方执行的偏差,尤其在新冠疫情影响尚未完全消退的背景下,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苛捐杂税、政策脱离实际,侵蚀的不仅是民众财富、企业活力,更是政权根基;而轻徭薄役、民生为本、紧跟中央部署的治理,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每一位公务员都应摒弃官僚主义、放下权力傲慢,将“主动作为、落实中央政策、服务群众企业”刻进岗位意识——让政策调整贴合经济脉搏、呼应中央要求,更契合疫情后民生与企业的真实需求,让决策充满民生温度,唯有如此,才能守住基层治理底线,赢得群众与市场主体的信任,让类似丰城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让国家在民生兴旺、企业活力迸发的基础上走向持久繁荣。 此外,俗语言“政通则人和,政兴则国昌”。政令不畅,小则影响决策落地,大则妨碍国家发展。严明的纪律是我们党领导革命与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唯有做到“党中央有令则行,动如雷霆;党中央有禁则止,稳若泰山”,才能形成无坚不摧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部署,再好的政策也将沦为空中楼阁。民间早有谚语讽喻:“中央政策大晴天,下到地区起点云,传到县里变成雨,落到镇里淹死人”“村骗乡,乡骗县,一路骗到国务院”。直至今日,“文件层层念,念完进饭店,执行不见面”的现象仍未绝迹。 一些地方官员对上一套、对下另一套,于地方或己有利则行,无利则拖、甚至顶风违纪。这实质是利益观的错位与颠倒。于局部,是本位主义、保护主义作祟;若蔓延全国,则将严重侵蚀国家治理效能,轻则积累民怨,重则动摇政权根基。因此,党必须下决心以强力措施确保政令畅通,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中央权威的同时,推动政策公开、接受人民监督。对那些不作为、乱作为、拒不执行中央政策的官员,必须依纪依法严肃问责,绝不姑息。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