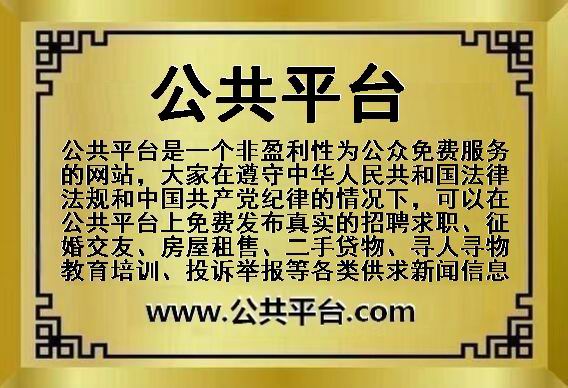|
|
陈中华:百姓被盘剥到活不下去之时,造反叛乱就成了唯一的出路
在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里,“盛世”与“乱世”的交替似乎是个无解的循环。有观点以金融与权力的双重视角,撕开了这层循环的本质——所谓盛世,不过是皇帝暂时压制住官僚集团的贪婪,给了老百姓一次喘息的机会。而这背后,是一场关于“皇帝、官僚、老百姓”三方的财富分配博弈,持续了整整五千年。 盛世的开端:让老百姓有钱赚 所有盛世的起点,都绕不开“富民”逻辑。汉文帝继位时国库空虚,他选择了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减税,轻徭薄赋。甚至有一年直接宣布“全年免税”,让老百姓从“将所有收成上交朝廷”的生存压力中解脱。 当百姓手里有了余钱,自然会尝试经商、扩大生产,财富在市场交易中被不断创造,国家反而因经济活跃而愈发富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它证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藏富于民,才是国家真正的繁荣根基。 盛世的终结:官僚集团的贪婪反噬 可惜,这种平衡极其脆弱。因为有一群人等不及要分走百姓的财富——官僚集团。 他们看着民间财富增长,却因皇帝的减税政策无法直接牟利,便开始了各种“操作”:巧立名目收苛捐杂税,在交通要道设置关卡抽成,甚至垄断盐、铁等生活必需品的买卖。表面上朝廷税率没变,老百姓实际承担的税负却可能翻了几倍。 有个触目惊心的数据:北宋官方规定税率仅10%,但百姓实际负担高达70%。中间那60%的差额,被各级官员层层“加码”,最终落入了私人腰包。皇帝在朝堂上高喊“轻徭薄赋”,官员却在基层闷声发大财。 当百姓被盘剥到“活不下去”时,叛乱就成了唯一的出路。造反成功后,新的皇帝又会重启“减税养民”的循环,盛世看似重现,可官僚集团的贪婪从未消失,于是历史又一次进入“繁荣—剥削—崩溃—重启”的闭环。 变法案例:政策的善意与执行的扭曲 有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案例,当属某次变法。变法者看到民间商人放高利贷,利率高达100%,许多百姓因还不起钱而破产。他提出一个构想:由国家放贷,将利率降至20%,既帮助百姓摆脱高利贷陷阱,又能增加国库收入。 政策初衷是良善的,但执行环节彻底变了味。地方官员为完成放贷任务,开始强制百姓借贷:不借就是“不配合朝廷政策”,会被扣上罪名;借了还不起,官员就“连本带利催收,收不上来就抓人”。原本的惠民政策,成了官僚集团新的盘剥工具。 这场变法最终加速了王朝的衰落,也留下一个残酷的教训:政策的好坏,往往取决于执行它的人。一旦权力缺乏约束,再善意的政策都会沦为敛财的武器。 五千年循环的底层逻辑:财富总量的零和博弈 有观点点破了历史循环的本质:“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 社会财富的总量是有限的,官僚集团拿多了,百姓就必然变少。当百姓被榨干到极限,国家体系就会崩溃——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数学不允许”的必然结果。 对官僚个体而言,他们的选择是“理性”的:多捞一点,国家不会立刻垮掉;等国家真的要垮了,自己早已捞够资本,可以全身而退。每个人都觉得“问题不在自己”,可当所有人都这么做时,整个系统便会一起陪葬。 历史的真相:不是王朝更替,是财富分配游戏的崩盘 我们总以为王朝更替是因为皇帝昏庸、外敌入侵或天灾人祸,可这些都是表象。真正的根源,是财富分配的游戏彻底崩盘了。当官僚集团把百姓逼到生存底线以下,整个系统就会“重启”——不是因为道德沦丧,而是经济规律的必然惩罚。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场永不落幕的分钱游戏。我们读历史,看到的是王朝兴衰、英雄辈出,可透过金融与权力的透镜,看到的却是“皇帝、官僚、百姓”在财富天平上的永恒拉扯。盛世的短暂与乱世的漫长,不过是这场拉扯中一次次失衡与重建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