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中华:绝不能把未成年人保护法,变成保护未成年人犯罪法
当 14 岁的潘某某在自家楼栋门口倒在血泊中时,那个本应充满书香与欢笑的花季彻底凋零。这起发生在深圳龙华的恶性案件,不仅是一个家庭无法承受的悲剧,更像一把尖刀,刺破了 “年龄即免责” 的虚幻保护壳,让 “绝不能把《未成年人保护法》变成保护未成年人犯罪法” 的呼声,成为全社会必须直面的严肃命题。 一、案件细节:“早熟的残忍” 颠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认知 凶手钟某的行为,早已超越 “一时冲动” 的范畴,尽显精心策划的恶意。他与被害人同班同住,长期受对方家长顺路接送的恩惠,却因生活琐事不满便痛下杀手。其犯罪过程的每一步,都透着对生命的漠视与对法律的算计:事先网购黑色折叠刀,刻意搜索 “14 周岁杀人需要承担什么责任”;首次捅刺潘某某后,听到呼救竟折返补刀,彻底断绝对方生路;事后还编造 “见义勇为被人砍伤双手” 的谎言,企图蒙混过关。 庭审中的细节更显其虚伪。钟某及其辩护律师试图以 “遭受校园欺凌” 脱罪,却被所有老师的证词和同学的证言戳穿 —— 事实恰恰是他长期欺负他人。直到被害人母亲提出 “判处死刑” 的诉求时,他才害怕得磕头求饶,这种迟来的 “悔意”,本质是对刑罚的畏惧,而非对生命的敬畏。 二、现实痛点:“年龄保护伞” 下的恶意与漏洞 “如果未成年人杀人不偿命、老人犯罪不受罚,那是不是花钱雇个孩子或老人,就能明目张胆地行凶?” 这个看似极端的假设,却精准戳中了当下法律实践的痛点。当 “年龄” 成为犯罪的挡箭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初衷便被扭曲。 这部法律的核心是 “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这里的 “未成年人”,首先是像潘某某一样的无辜受害者,而非侵害他人的施暴者。但现实中,部分未成年人犯罪已呈现 “明知故犯” 的恶意:沈阳地下通道的施暴者,明知售卖暴力视频会传播危害,却标价 50 元赚 “快钱”;江油少年撕扯同学衣服时,清楚脱衣羞辱会造成精神伤害,却对着镜头狂笑;江西万载围殴者,明知拳头会打断骨头,仍故意朝着要害下手。 更危险的是 “年龄漏洞” 可能被恶意利用。近年来,多地已出现 “成年人指挥未成年人盗窃”“利用未成年人运输毒品” 的案件,正是钻了 “年龄豁免” 的空子。若对这种恶意视而不见,法律便成了犯罪集团的 “作案工具”。 三、数据警示:低龄暴力犯罪 “早熟化”“恶性化” 趋势 潘某某的悲剧并非孤例,而是低龄暴力犯罪趋势的缩影。最高检数据显示,2018 至 2022 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 14 至 16 周岁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年均上升 7.3%,其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重罪占比超 20%;2020 至 2024 年,14-16 周岁未成年人实施恶性犯罪的案件年均增长 12.3%,有组织犯罪占比达 34%,不少案件呈现 “分工明确、事后销毁证据” 的成熟模式。 这种趋势背后,是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与认知水平的变化。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青春期发育年龄较上世纪 90 年代提前 2-3 年,12 岁少年的身高、体能已接近成年;互联网更让信息获取无门槛,13 岁孩子通过短视频就能学会 “规避法律制裁”“隐藏作案证据”,对犯罪后果的认知甚至超过成年人。当孩子的 “恶意” 已与成年人无异,法律若仍固守旧标准,就是对生命的漠视。 四、法治共识:对恶性犯罪的宽容绝非文明象征 回望历史与世界,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 “零容忍”,从来都是法治文明的共识。我国唐代《唐律疏议》就规定,10-15 岁杀人 “必须死刑,没得商量”,8-10 岁杀人若情节恶劣,需奏请皇帝裁决,而非直接豁免;伊朗法律要求少年杀人者,男性监禁至 15 岁处决,女性至 18 岁处决;新西兰 14 岁男孩因残忍杀害流浪汉,被判处 “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美国部分州对 13 岁以上实施恶性犯罪的未成年人,允许按成年人标准量刑。 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原则:对生命的尊重、对正义的维护,永远高于 “年龄豁免” 的形式主义。当一个孩子举起屠刀时,社会更该思考 “如何让他为生命负责”,而非 “如何帮他逃脱惩罚”。2024 年河北邯郸 “13 岁少年杀人埋尸案” 中,无期徒刑的判决让公众看到了司法的严肃力量,也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重要参照。 五、破局方向:构建 “犯罪必担责” 的法律闭环 要扭转 “年龄即保护伞” 的现状,法律修订与执行必须迈出实质性步伐。 下调刑事责任年龄,明确 “恶意” 标尺:建议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调整至 8 岁(《民法典》已明确 “不满 8 周岁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 岁以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 “伤害他人” 缺乏基本认知;8 岁以上未成年人已能分辨 “打人会痛”“杀人会死”,其主观恶意应被法律认可。8-12 岁实施恶性犯罪者,送入专门矫治机构接受至少 3 年强制矫正,记录入 “未成年人犯罪档案”;12 岁以上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等重罪者,直接适用刑法,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建立连带追责机制,压实监护与教育责任: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是监护失职与学校教育缺位的结果。建议明确:父母需承担全部民事赔偿,情节严重者(如多次纵容、教唆)追究刑事责任;学校若存在 “明知欺凌不处理”“未开展法治教育” 等失职行为,校长与直接负责人应被撤职,学校纳入 “教育黑名单”。 强化矫治教育的惩戒性,杜绝 “走过场”:现行 “批评教育”“家长带回” 等措施形同虚设。专门学校应配备心理矫正师、法治教官,实施 “军事化管理 + 心理干预 + 技能培训” 的综合矫治,定期评估改造效果,未达标的延长矫治期,让 “矫治” 真正带 “痛感”。 六、回归本质:保护善良,而非庇护罪恶 “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前提是儿童成长为尊重生命、遵守法律的好人。若法律纵容孩子行凶作恶,培养出的只会是危害社会的 “未来罪犯”,这绝非立法的初衷。当 14 岁的潘某某再也无法回到课堂,当受害者家属只能对着墓碑流泪,法律必须用公正的判决告慰逝者 —— 年龄从来不是犯罪的 “护身符”,触碰法律红线必受严惩。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底色是 “正义”,而非 “纵容”。唯有让法律的锋芒划清 “不可逾越的红线”,让每个孩子懂得 “年龄再小,也不能践踏生命;力气再弱,也不能伤害他人”,这部法律才能真正成为 “保护善良的盾牌”,而非 “庇护罪恶的温床”。期待深圳这起案件的最终判决,能彰显司法的力量,为所有未成年人敲响警钟,让 “无妄之灾” 不再重演。 原中国政法大学公正司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中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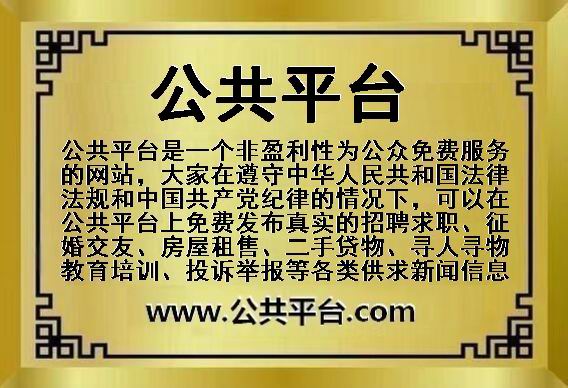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