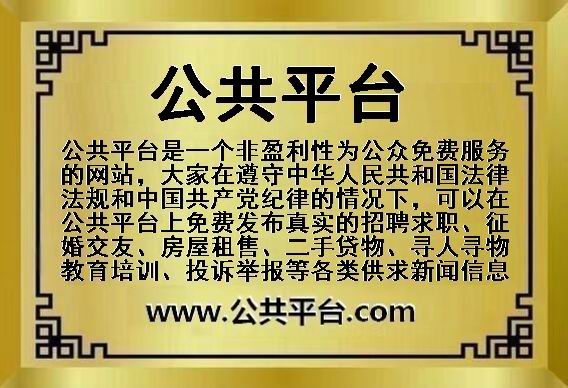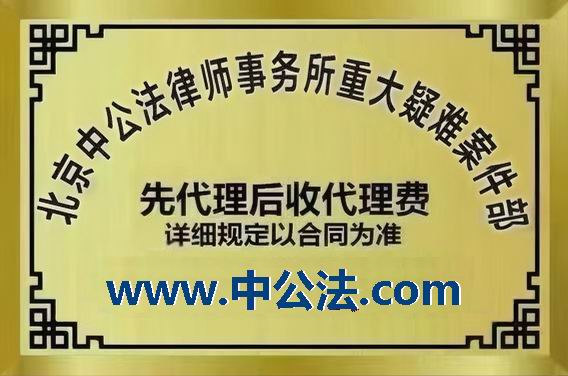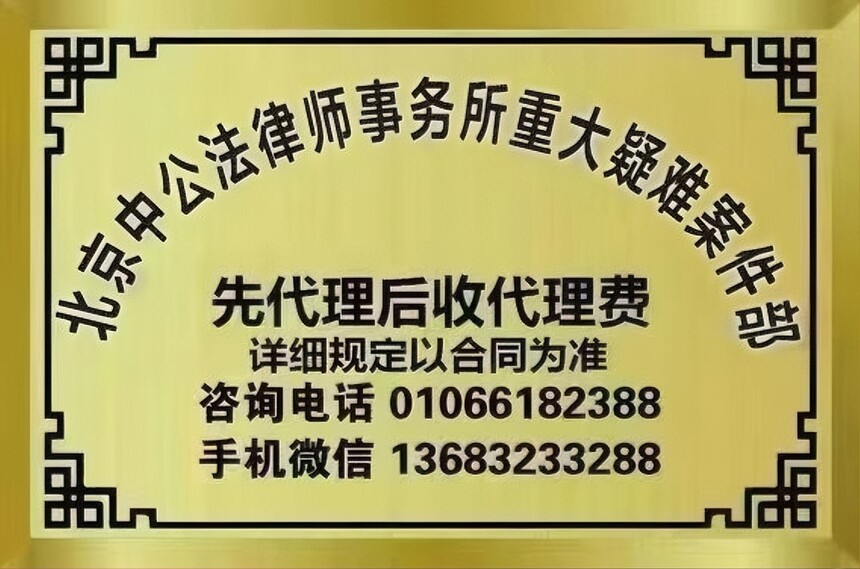|
|
陈中华: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
近日,一则旧闻令人深思:原河南省平舆县法院院长刘德山曾蒙冤入狱,在看守所被羁押百余天,期间遭遇刑讯逼供。重获自由后,他发出沉痛反思: “我从事司法审判近三十年,审理过近千起刑事案件。法庭之上,被告人无数次声称遭遇刑讯逼供,我却一次都未曾采信。如今亲身经历才真正读懂法律,也才明白普通人的无助。我过去的所作所为,堪称罪人。此番遭遇,亦是天道轮回的报应。” 这位深耕司法多年的资深法官,尚且难以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不禁让人追问:连法官都维权无门,普通百姓又当如何? 类似的荒诞与刺痛,并非孤例。 2010 年 6 月,湖北省委大楼前发生一起恶性围殴事件:女子陈玉莲按约前往政府大楼会见友人,在门口正常等候、配合核验时,突然被六名男子暴力围殴长达十多分钟。她多次表明身份,却被对方嗤之以鼻,持续遭到殴打,最终造成脑震荡、多处骨折与全身淤青。 直到其丈夫 —— 时任省政法委副主任赶到现场,施暴者才惊觉,他们殴打的是干部家属。事后查明,施暴者为负责信访秩序的工作人员,只因误判便肆意动用暴力,即便面对劝阻也毫无收敛。若不是身份特殊、事件闹大,一句 “奉命行事”,恐怕就能轻易掩盖真相。 此事最令人不安之处在于:连干部家属尚且遭受如此对待,普通群众在类似场景下,又能得到多少尊重与保护? 比个案更令人警醒的,是蔓延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信任崩塌与道德失序。 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种子假化肥、假文凭假身份、假证明假履历…… 假冒伪劣渗透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每一环。网友自嘲式的段子道尽无奈: “早起吃添加剂油条,中午吃问题肉类,晚上睡黑心棉被,一天都在‘服毒’中度过。” 本应传道授业的教师,有人将心思放在牟利与补课之上; 本应救死扶伤的医者,有人在处方与手术中追逐利益; 本应清净庄严的寺庙,沦为明码标价的求财场所; 本应为民服务的公权岗位,却有人将权力异化为谋私工具。 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令人窒息的 **“互害循环”**: 卖毒大米的人,吃着问题牛肉;生产假酒的人,孩子喝着问题奶粉;制造有害食品的人,又被另一套骗局收割。人人精明算计、趋利避害,却又在无形之中彼此伤害,最终无人能独善其身。 比 “互害” 更可怕的,是“杀善”—— 善良被嘲讽、见义勇为被追责、热心助人反被讹诈、真诚信任屡屡被利用。 退伍军人赵宇见义勇为制止侵害,嫌疑人未被严惩,出手相助者反而先被拘留、再被追责,上演 “英雄流血又流泪”。 路人跌倒无人敢扶,不是人心冷漠,而是善良被一次次消耗; 群众乐善好施,却屡屡遭遇职业乞讨、虚假求助,善意被当成牟利工具。 当行善成本极高、作恶代价极低,社会便会批量生产麻木的看客。 百年前,鲁迅痛心于国人麻木,弃医从文唤醒良知;百年后,冷漠与旁观依然随处可见。 善良被扼杀,正义被悬置,底线被击穿,最终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安全感与幸福感。一个连同胞都不敢信任、不愿善待的社会,再谈民族复兴,无异于空中楼阁。 人性本有善恶两面,好的制度约束恶行,坏的制度放纵恶念。 当 “修桥补路无尸骸,杀人放火金腰带” 成为现实写照,当老实本分被视作无能,投机钻营反而风生水起,社会便会滑向丛林法则。 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司法的腐败不公。司法活动承担着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人们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等各项权益的保障,以及国家、政权、社会的稳定都与司法活动密切相关。司法腐败是对党和国家、对人民危害最大的腐败。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司法工作人员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 能让该死的人不死该活的人不活。 司法腐败不公,它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对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造成致命伤害,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司法不公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机体内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党的政权。 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是早有结论的,但是如今许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反面的例子是清末的多次对外应战,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决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要严惩不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社会才能稳定发展,民才能幸福生活,党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而长期执政。 东方政法服务中心主任陈中华
|